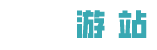《纪念碑谷》是这几年我玩过的最优秀的一款游戏。这是一款与喧闹、躁动和享乐绝缘的游戏,它孤独、冷静,却不失温情,精致神秘得让人惊叹。
在玩的时候我也隐约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空间艺术感,看过埃舍尔的画再去玩《纪念碑谷》的人会有一种熟悉感,能够强烈感受到设计团队对埃舍尔大师的致敬。因为我本身对视觉文化里面的视错觉比较感兴趣,所以花了点时间仔细看完埃舍尔的作品集以及他作品背后的故事,丰富了自己对《纪念碑谷》所表达的“意义”的理解,在此跟大家分享我一点小小的“玩”后感。
一、向视错觉大师致敬
游戏中除了主角艾达公主与幽灵的对话之外,没有其他的文字对话。与大部分游戏的主题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让用户到处拣取“财富”,追逐胜利,而是安静地探寻与归还。网上有不少人写文章解读《纪念碑谷》的主题,我比较认可的一个解读是:艾达公主穿梭在迷宫般的神殿中,一一归还她盗走的神圣几何体。在这一游戏中无论是建筑,人物,还是风景、器物,都带着神秘的抽象感和荒谬感,仿佛孤独的主角探寻穿梭的,其实是一件件的艺术品。《纪念碑谷》的作者曾说他们投注无数精力打造的这一作品是像错觉大师埃舍尔(M.C.Escher)致敬,玩家在游戏过程中能够看到无数埃舍尔作品的影子。就像身临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
比如在第十章《观象台》中,主角要在这个“不可能立方体”的建筑中寻找分别导向柱子上三个门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自体验到了“行走”在这个不可能结构上的荒诞和精妙。就像是埃舍尔《另一个世界》中从不同角度看的空间,这幅四色木刻给人视觉上诡异的冲击感:观者会发现自己处在一间“上”、“下”、“左”、“右”、“前”、“后”的概念随时变化的屋子里。游戏的乐趣在于,它把我们只能在二维上看到的埃舍尔画中的神奇三维建筑变为鲜活的,可转动,可探索的空间。埃舍尔的《观景楼》中,错觉让我们看到顶楼仿佛是被8根诡异交错的柱子稳稳承接着,但事实上顶部贵妇人所在的那层楼其实是悬着的。
《纪念碑谷》第十章“观象台”
埃舍尔《另一个世界》(Other world)
埃舍尔《观景楼》( Belvedere-1958 )
在游戏场景中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场景,走到一段路的尽头,仿佛这段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它没能连向任何另一处地方,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角度观看这个建筑,总能找到视觉上连接在一起的路径,在这个“不可能世界”中,眼见的合理即合理,眼见不一定为实,也不一定为虚,这也是《纪念碑谷》吸引人的地方:于虚实之间探索出路,发现行走的新方式。
《纪念碑谷》最受人欢迎的一章“盒子”
《纪念碑谷》类似《相对性》的迷乱空间
埃舍尔《相对性》(Relativity)
因为接触了《纪念碑谷》,我才重新把埃舍尔的作品集拿出来仔细欣赏,如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曾让你惊奇不已,你会在《纪念碑谷》中深切感受到曾经的惊奇鲜活在指间那种妙不可言的美。《盒子》那一关卡我大概花了五分钟左右就通关了,但是它留给我的震撼历久弥新。这一关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机关“暗器”,又有点埃舍尔版画《相关性》的影子。其实他很多的画我起初是看不懂的,只能朦胧感知到一种错觉迷乱带来的惊奇和震撼,后来我在恩斯特著的一本记载埃舍尔生平和作品的书《魔镜——埃舍尔德不可能世界》(The magic of M.C.Escher)中看到了埃舍尔本人对他作品的一些介绍。我才知道原来这幅《相对性》有三个灭点,“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怪异却又看似真实的整体。埃舍尔留给观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些行走在不同维度世界的人们会相遇吗?他们看得到彼此吗?往前走下去这个人能进入他人的花园里吗?怎样走才能最快抵达自己空间的花园?有太多的故事,就藏在这一错觉空间中。在《纪念碑谷》中我已经习惯地接受行走在交错空间的可能。眼见现实与虚幻的物理规律纠缠在一起,视觉所确定的连接即可畅通无阻,实在是美妙!
二、错觉艺术与美
错觉为什么总给人不可言说的美感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拥有了无限遐想及希冀的空间。就像郑愁予诗中“哒哒”的马蹄声,让人怀抱着“归人”或是“过客”的无限遐想。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提到了错觉的起源:古罗马时期真正出现了柏拉图反对的“欺骗眼睛的幻觉艺术”。在《魔镜》一书中,作者同样认为“绘画即骗术——即,暗示代替了现实——我们便可以得寸进尺,用一个二维的世界创造出一个三维的世界……一方面,埃舍尔在各种作品中展示这种骗术;另一方面,他完善了它,把它变成一种超级幻象,使之呈现出不可能的事物,由于这种幻象是如此地顺理成章、不容置疑、清晰明了,这种不可能便造就了完美。”(《魔镜——埃舍尔德不可能世界》(The magic of M.C.Escher)布鲁诺.恩斯特著,田松、王蓓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24-25)埃舍尔的作品带着强烈暗示的空间感,《纪念碑谷》也是一样,这些变形、循环、无穷和不可能的世界,都在传达一种错觉的惊奇。埃舍尔曾说“惊奇”正是他追求的首要目标。他“尽力唤醒观众头脑中的惊奇”。《纪念碑谷》全部关卡体验一遍之后,和看完埃舍尔德作品一样,我越是久久凝望,它们在我心里唤醒的惊奇和敬畏越是不断增长。我最多的惊叹要献给《纪念碑谷》的“静谧庭院”一章及埃舍尔的《瀑布》,事实上,它们共享同一美的灵魂。
《纪念碑谷》遗忘的海岸第四章“静谧庭院”
埃舍尔《瀑布》(Waterfall-1961)
在《魔镜》一书中,作者纪录了埃舍尔对抽象数学立体和晶体的着迷。埃舍尔偶然看到彭罗斯的三杆而引发创作石版画《瀑布》的灵感。建筑中的瀑布从高处流下水车,在水车转轮的作用下又沿着石路流动循环到高空又冲下水车,这个建筑结构实际上是由两个彭罗斯三杆构成,有一种循环、无穷与自我迷失的意味。在《纪念碑谷》静谧庭院这一章中,设计师巧妙地把《瀑布》的场景重现。在《瀑布》这幅画中,两个顶楼分别放置着两个复杂的立方体。在埃舍尔的另一幅画《群星》中,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谷》里面主角到达每一个目的地之后归还的“神圣几何”的原型。
埃舍尔《群星》中的几何多面体
彭罗斯的三杆
《纪念碑谷》中的截图-彭罗斯三杆
三、观看、孤独和美
在玩《纪念碑谷》这款游戏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孤独和讶异,这是关于一个人的探寻与发现,迷失与惊喜。矛盾的是,我多想在此时此刻的深夜叫醒好友们,跟大家分享这份惊讶。看《纪念碑谷》的画面和看埃舍尔的画,都有一种优雅的孤独感和自我反省。记得在《纪念碑谷》中有一个画面,主角艾达公主路过一面镜子,镜子里面她的镜像是一只戴着皇冠的白鸟。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个镜像的意思。直到最后一章游戏结束时,艾达归还了所有的神圣几何体,她身上的诅咒破除了,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她的原貌正是那只戴着皇冠的白鸟。原来这是一场寻找救赎,回归真我的旅途。《纪念碑谷》在像埃舍尔致敬的同时,把孤独的美诠释得更为优雅。埃舍尔对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说过他想竭力表达自己“看到”的东西,他在一封信里写道“如果你能知道我在黑夜之中看到的东西就好了……有时,我因为不能以视觉符号表达它们而感到焦躁、沮丧。与那些思绪相比,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失败的。甚至,连它们的一角都表现不出来……当我开始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想,我正在创作全世界最美的东西”(《魔镜》)这种孤独和美始终贯穿着埃舍尔创作的主题。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自己是一个“内向”、“难与陌生人相处”、“需要独处”的人。埃舍尔在自己创作的那些自我缠绕的不可能空间中享受着宁静和孤单,用自己的角度观看着世界并创造出被观看的世界。
《纪念碑谷》中出现的镜子

《纪念碑谷》中的“蛇”

《纪念碑谷》的世界把埃舍尔创作的“不可能世界”精妙地重构出来,可多角度“观看”,可“行走”游荡其间,可探索无穷循环,可无视谬误走向终点……行走在虚实之间,满足视觉的合理即可畅行无阻。在这个指尖空间中,传统的空间观念限制和理性视野樊笼被一一破除,只剩惊奇。
所以,如果你要在其中寻找“意义”,去翻翻埃舍尔吧。
关于“观看”、“错觉”和“镜像”我了解不深,只能浅浅提一下,大家可以在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等著作了解更多。